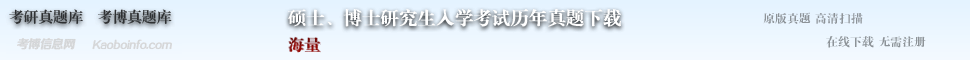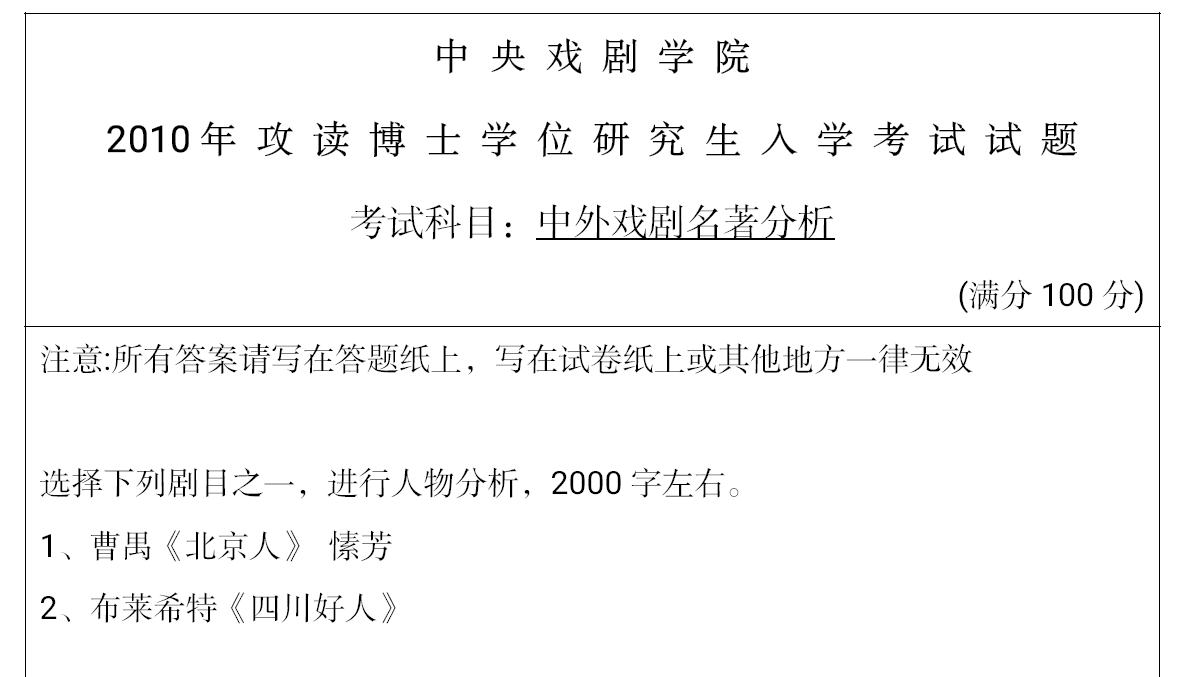
中央戏剧学院 2010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
考试科目:中外戏剧名著分析
(满分 100 分)
注意:所有答案请写在答题纸上,写在试卷纸上或其他地方一律无效
选择下列剧目之一,进行人物分析,2000 字左右。
- 曹禺《北京人》 愫芳
- 布莱希特《四川好人》
答案核心框架:愫芳是曹禺以 “心灵塑造” 的经典女性形象,其性格呈现 “隐忍 — 觉醒 — 突破” 的三层递进,既是旧时代封建家庭中女性的悲剧缩影,也是传统美德与现代觉醒碰撞的精神符号。
曹禺在《北京人》中塑造的愫芳,并非传统家庭剧里 “逆来顺受的牺牲品”,而是以 “隐忍为表、觉醒为核、突围为终” 的复杂女性形象。她的命运轨迹既是旧中国封建士大夫家庭的精神缩影,也是传统女性在时代转型中 “从依附到独立” 的现代性启蒙,其形象的深度在于:曹禺以 “鸽子意象” 为隐喻,让愫芳在 “鸟笼” 般的曾家中完成了 “留守 — 审视 — 飞走” 的精神蜕变,最终成为旧时代的 “叛逃者” 与新女性的 “启蒙者”。
愫芳的出场便带着 “依附者” 的底色:父母双亡后寄养在曾家,以 “姨侄女” 的身份承担起照料病弱姑父曾皓的责任,成为曾家 “离不开的拐杖”。她的 “隐忍” 并非被动妥协,而是带有传统礼教规训下的 “主动牺牲”—— 她将 “温良恭顺” 内化为自我要求,以 “宁肯自己受苦,也要让别人安乐” 的逻辑,在曾家的压抑氛围中维系着脆弱的平衡。
曾思懿的刻薄是愫芳隐忍的直接催化剂:作为曾家的 “当家主母”,曾思懿视愫芳为 “抢占曾家资源的外人”,时常以 “三十岁还没嫁人”“赖在曾家吃白饭” 等言语讥讽她。但愫芳的回应始终是 “低头做针线,不说话”—— 这种沉默并非麻木,而是她对 “家族伦理” 的主动维护:她深知曾家已是 “风雨飘摇的破屋”,自己的反驳只会让矛盾激化,不如以沉默换 “表面的安宁”。
更深刻的牺牲,在于她对曾文清的 “情感供奉”。愫芳将曾文清视为 “灵魂的知己”:曾文清的诗词书画、文人雅趣,是她在压抑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慰藉;她甚至将曾文清比作 “能飞出笼子的鸽子”,自己则甘愿做 “留守鸟笼的那只”—— 她替曾文清打理书房、收藏字画,替他承受曾皓 “传宗接代” 的压力,将曾文清的 “文人梦想” 当作自己的人生寄托。这种 “以爱人的梦想为梦想” 的牺牲,本质是传统女性 “依附男性价值” 的体现,但也暗含着愫芳对 “自由生活” 的间接渴望:她将曾文清的 “出走” 视为自己 “逃离曾家” 的替代,在对他人的期待中,藏着自己不敢言说的 “突围欲”。
愫芳的觉醒,始于曾文清 “出走又归来” 的荒诞闹剧。她曾对曾文清的 “离开” 抱有极致的期待:“我总想着,他走了,他会过一种新的生活,一种有意义的生活”——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:她希望曾文清的 “成功”,能证明 “曾家之外有另一种人生”,从而为自己的 “逃离” 提供合理性。
但曾文清的 “归来” 彻底击碎了她的幻想:曾文清在外闯荡不足一月,便因 “受不了外面的风浪” 逃回曾家,甚至连 “谋生的本事都没有”。当曾文清蜷缩在书房里,颤抖着点燃鸦片时,愫芳终于看清:曾文清并非 “能飞的鸽子”,而是与曾家一同腐朽的 “空壳文人”—— 他的 “文人雅趣” 不过是逃避现实的 “精神鸦片”,他的 “出走” 也只是 “懦弱者的短暂逃离”。
这种认知的崩塌,让愫芳的 “隐忍” 转向 “审视”。她开始重新解读曾家的 “日常”:曾皓的 “孝道绑架”(以 “我死后谁送终” 逼迫愫芳留下)、曾思懿的 “刻薄算计”(为争夺家产排挤他人)、曾家上下 “耗子般的苟活”(剧本中 “耗子偷油” 的隐喻),都不再是 “需要包容的家族矛盾”,而是 “吞噬人性的牢笼”。此时的愫芳,沉默中不再是妥协,而是对旧生活的 “价值否定”—— 她终于意识到,自己此前的牺牲并非 “美德”,而是对 “虚幻情感” 的执念,对 “腐朽制度” 的纵容。
愫芳的最终 “突围”,以 “带着曾瑞贞出走” 的方式完成,这一行为让她的形象超越了 “个人逃离”,成为旧时代女性的 “启蒙者”。
曾瑞贞是曾家中的 “新青年”:她接受进步思想,不满曾家的封建礼教,甚至怀有身孕仍计划离开。愫芳与曾瑞贞的 “结盟”,是 “觉醒者” 与 “行动者” 的互补:愫芳的 “觉醒” 是精神层面的 “认知颠覆”,曾瑞贞的 “反抗” 是实践层面的 “行动指引”。当曾瑞贞问她 “你敢不敢跟我走” 时,愫芳的回答是 “敢!我早就想走了”—— 这句话的 “早” 字,呼应了她此前对曾文清的 “期待”,但此时的 “走”,已不再是 “依附他人的逃离”,而是 “自主选择的新生”。
曹禺刻意让愫芳 “带着瑞贞走”,而非 “独自离开”,其深意在于:愫芳的 “出走” 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突围,更是对 “女性互助” 的倡导。她不再是 “曾家的拐杖”,而是 “引领同类的火把”—— 她带着曾瑞贞走向 “未知的新社会”,既是自己的 “新生”,也是对其他女性的 “启蒙”:她证明,旧时代女性的出路,不是 “等待男性拯救”,而是 “与同类结盟,主动打破牢笼”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愫芳的 “出走” 没有明确的 “目的地”,但曹禺以 “远处传来的火车声” 作为背景音 —— 火车是 “现代文明” 的象征,这一意象暗示:愫芳的 “突围” 并非 “无目的的逃离”,而是走向 “现代性的新社会”。她的 “出走”,是旧时代女性从 “封建依附” 到 “独立人格” 的转型,是传统美德(善良、坚韧)与现代思想(自主、平等)的融合。
曹禺创作《北京人》时,正值抗战时期(1941 年),民族的 “存亡危机” 与个体的 “生存困境” 相互交织。愫芳的形象,既是对旧中国封建家庭女性命运的悲悯,也是对 “民族觉醒” 的隐喻 —— 她的 “突围”,暗合着民族从 “腐朽沉沦” 到 “主动新生” 的期待。
从 “鸟笼中的鸽子” 到 “带着瑞贞飞走”,愫芳的蜕变证明:旧时代女性的觉醒,从来不是 “突然的反抗”,而是 “隐忍中的积累、审视中的颠覆、互助中的突围”。她的形象,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中 “女性精神成长” 的经典标本,其 “从依附到独立” 的轨迹,也为解读旧时代女性的命运提供了深刻的参照。
答案核心框架:沈黛与崔达的 “正反同体” 是布莱希特 “陌生化效果” 的经典实践,通过 “善良妓女” 与 “冷酷老板” 的身份切换,揭露 “社会异化人性” 的荒诞现实,指向 “改变社会才能改变人” 的核心命题。
布莱希特在《四川好人》中以 “沈黛 / 崔达” 的双重身份设定,打破了传统戏剧 “好人 / 恶人” 的二元对立,通过 “善良妓女” 与 “冷酷老板” 的身份切换,揭露了 “社会环境异化人性” 的核心命题 —— 沈黛的 “善” 不是 “天性软弱”,崔达的 “恶” 不是 “人性本坏”,二者的同体存在,本质是畸形社会下 “生存逻辑碾压道德选择” 的荒诞缩影。
沈黛是布莱希特以 “底层善良者” 为原型塑造的 “道德标本”,却被放置在 “道德失序的社会” 中,成为 “善被剥削” 的典型。
她的 “善” 带有 “不计回报” 的纯粹性:作为成都贫民窟的妓女,她在自身温饱难继时,仍将高价嫖客打发走,为三位 “寻找好人” 的神仙提供免费住宿;获赠一千银元后,她放弃 “改善自身生活” 的本能,开设 “亲民烟店”,意图 “以善养善”—— 她给底层穷人赊账、收留无家可归的木匠、给失业者提供工作,甚至对敲诈勒索的欣夫人也一再退让。布莱希特刻意将沈黛的职业设定为 “妓女”,以世俗眼光中的 “边缘者” 承载 “最高的善”,形成 “身份污名” 与 “道德高光” 的反差,解构了 “道德与社会地位绑定” 的偏见。
但沈黛的 “善” 从一开始就注定失效。她的烟店迅速沦为 “底层者的寄生场”:木匠以 “干活” 为名白吃白住,欣夫人以 “借钱” 为由敲诈钱财,烟店伙计不仅偷懒还私吞货款 —— 在物质匮乏、规则缺失的贫民窟,“纯粹的善” 成了 “可被无限索取的软肋”。当烟店濒临破产时,沈黛哭诉 “我想做好人,但好人活不下去”,这句话直指核心:她的困境并非 “个人能力不足”,而是社会机制的扭曲 —— 在一个 “弱肉强食” 的环境中,“善” 不是 “生存资本”,而是 “被吞噬的诱饵”。此时的沈黛,是 “道德理想” 被 “现实逻辑” 碾碎的牺牲品。
崔达的出现,是沈黛 “被迫的生存选择”,却成了 “人性异化” 的标本。
为拯救烟店,沈黛女扮男装,以 “表兄崔达” 的身份回归。崔达的 “恶” 是对 “沈黛之善” 的彻底反拨:他驱逐了白吃白住的木匠,将欣夫人的债务连本带利追回,压低工人工资、延长工作时间,甚至将烟店改为 “剥削式工厂”—— 短短数月,烟店从 “濒临破产” 变为 “财源滚滚”,崔达也成了贫民窟的 “新权贵”。但崔达的 “恶” 并非 “天性堕落”,而是对 “社会规则” 的反向适应:他清楚,在贫民窟的生存逻辑里,“善良 = 软弱 = 被吞噬”,只有 “冷酷 = 强大 = 能生存”。
布莱希特通过 “身份切换” 的细节强化 “异化” 的荒诞性:沈黛每次变身为崔达,都需要 “戴上帽子、换上男装、压低声音”,这一 “面具化” 的操作,既是 “陌生化效果” 的舞台实践,也暗示了崔达的 “恶” 是 “社会规训的产物”—— 崔达不是 “另一个人”,而是沈黛 “为了生存不得不戴上的面具”。当崔达对工人说 “我是好人,但好人得先活下去” 时,这句话是沈黛的 “生存宣言”,也是对社会的控诉:不是 “人选择了恶”,而是 “社会逼好人作恶”。
沈黛与崔达的 “同体存在”,是布莱希特对 “人性与社会关系” 的深刻追问:在畸形的社会中,“善” 与 “恶” 不是 “人性的二元对立”,而是 “生存的两种策略”。
二者的身份切换,本质是 “道德理想” 与 “生存现实” 的碰撞:沈黛代表 “人对善的本能向往”,崔达代表 “人对生存的本能渴望”,而社会的扭曲让这两种 “本能” 无法共存 —— 想 “善” 就无法 “生存”,想 “生存” 就必须 “恶”。三位神仙的 “寻找好人”,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:他们只要求 “人保持善”,却拒绝改变 “让善无法生存的社会”;当他们最终逼迫崔达 “交出沈黛” 时,沈黛摘下面具的呐喊 “你们要我做好人,但这个世界不让好人活”,彻底揭露了神仙(象征 “顶层统治者”)的虚伪 —— 他们关心 “道德符号的存在”,却无视 “道德实践的土壤”。
布莱希特并未给沈黛 / 崔达一个明确的结局:剧终时,沈黛仍在 “沈黛” 与 “崔达” 的身份间挣扎,神仙也未能给出 “如何做个好人” 的答案。这种开放式结局,正是布莱希特 “叙事剧” 的核心意图 —— 他不想让观众 “同情沈黛的悲剧”,而是让观众 “反思社会的荒诞”:当社会机制让 “善” 与 “生存” 对立时,“人性的扭曲” 不是个人的错,而是社会的病;要拯救 “好人”,不是 “要求人更善”,而是 “改变让善无法生存的社会”。
《四川好人》创作于 1943 年(二战期间),彼时欧洲正处于 “道德崩塌、生存至上” 的环境中。沈黛 / 崔达的形象,既是对 “战争中人性异化” 的反思,也是对 “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规则” 的批判 —— 她 / 他的困境,是现代社会中 “个体道德” 与 “社会逻辑” 冲突的缩影。
从 “沈黛的善” 到 “崔达的恶”,再到 “善恶同体的挣扎”,布莱希特以 “陌生化” 的手法,让观众跳出 “对人物的情感共情”,转而思考 “社会对人性的塑造”。沈黛 / 崔达的形象至今仍有现实意义:当我们讨论 “好人难做” 时,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 “人性的堕落”,而是 “我们是否构建了一个让好人能活下去的社会”。
中央戏剧学院《中外戏剧影视名著分析》考博真题(含 2010 年及历年试题)是备考核心资料,能帮助考生精准把握 “人物分析题” 的命题逻辑 —— 多围绕 “角色性格分层”“形象隐喻”“时代关联” 展开,需结合戏剧理论(如现实主义、陌生化效果)深化分析深度。考生可通过以下渠道获取真题及高分答案详解:
- 考博信息网官网:http://www.kaoboinfo.com/(可查询全国多所院校考博真题,含中外戏剧影视名著分析专项资料)
- 中央戏剧学院历年考博真题下载专用页面:http://www.kaoboinfo.com/shijuan/school/408061_1_2671171.html(可直接下载该校该科目真题,附详细答题策略)
-
人物分析题答题逻辑:“三层定位法”
- 第一层:角色的 “文本定位”(结合剧本情节、台词,梳理人物经历与性格);
- 第二层:角色的 “艺术定位”(分析作者塑造该角色的手法,如隐喻、象征、对比);
- 第三层:角色的 “时代定位”(关联作品创作背景,挖掘角色背后的社会意义或人性思考)。
例如分析愫芳时,需同时结合《北京人》创作于 1941 年(抗战时期)的背景,理解其 “出走” 暗含的 “民族觉醒” 隐喻。
-
名著积累:聚焦 “中西方经典 + 戏剧手法”
重点梳理曹禺(《雷雨》《日出》《北京人》)、老舍(《茶馆》)等中国现代剧作家,以及莎士比亚、布莱希特、易卜生等西方经典剧作家的作品,不仅记忆情节与人物,更需掌握不同戏剧流派(如现实主义、表现主义、叙事剧)的核心理论,确保分析时 “有理论支撑”。
-
模拟练习:对照真题答案优化表达
每周选取 1 道真题(如 2010 年愫芳分析题)进行完整写作,完成后对照考博信息网提供的高分答案详解,修正 “逻辑漏洞”(如是否遗漏角色的多面性)与 “学术规范”(如是否正确引用戏剧理论),提升答题的精准性与深度。